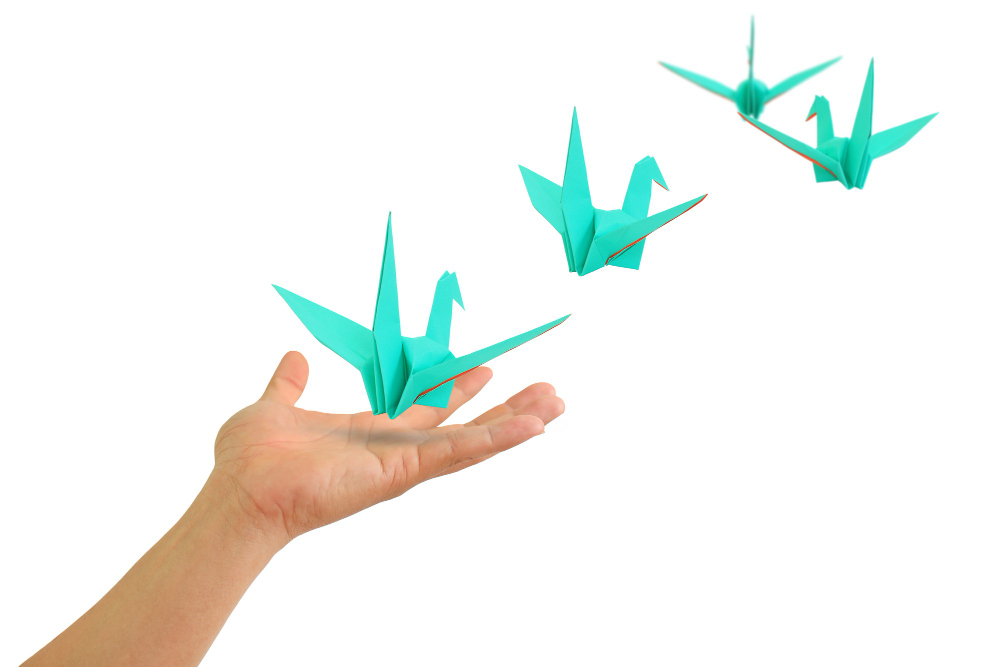
文/ 李文屏
四 人倒霉時
他正用吹風機上下吹干自己﹐誰知把老板也吹來了。老板年過半百﹐肩寬體壯﹐臉上沒有眼鏡﹐腰上也無幅度﹙福肚﹚﹐高興時眼睛放光﹐不高興時眼睛也放光﹐看上去讓人想到的是體育場而不是實研室。有他在旁邊一站﹐本來不高也不矮的李岩就立刻顯得瘦小﹐像白鵝旁邊的一只尷尬的濕公雞。老板一看明白他要看的﹐眼睛就發光﹐并沒有說什么﹐但象是什么都說了﹐吹風機在李岩的手上就再也呆不住。
第二天﹐李岩眼一睜就出了門。等快到李岩回家的鐘點時﹐張莉再三猶豫要不要給李岩做晚飯﹐最後還是做了。不做的話﹐他辛苦一天回來吃什么呢﹖嘔氣歸嘔氣﹐飯總還得吃吧。
然而飯菜慢慢涼了﹐李岩并沒有出現。後隨著夜色的加深﹐張莉的心也漸漸涼得像冰。
雨季的云塊大規模﹑黑漆漆地從太平洋移來﹐外面是個沒有星﹑沒有月的沉夜。當村子里最後一班公車的聲音從遠處到更遠處﹐張莉最後一點模糊的等待也就隨這最後一班公車去了。夜終於托不住沉重的黑云﹐雨就然突掉了下來﹐在每一盞昏黃的路燈下都快快地閃現著一片粗粗細細的銀絲。
凌晨的時候﹐電話響。張莉不想接﹐但還是接了﹐怕是什么壞消息。果然是懷消息﹐但不是她擔心的那種。電話那頭是老梁的聲音﹐說李岩在他那里﹐叫張莉不要擔心﹐他會勸李岩回來。
張莉說﹕「告訴他﹐永遠不要回來了。」
她的心變得出奇的空曠和寧靜。她環顧四周﹐房間里面已經罩著一層透明的陌生。
結束了﹐她留在美國的原因已經不存在了。
早上剛過八點﹐她就給一個大家稱為媛姐的朋友打電話。大家﹐是指參加媛姐家聖經學習的女人們﹐她們把這個聚會叫做姐妹會﹐因為信仰耶穌基督的女人彼此都叫做姐妹﹐一家人的意思。姐妹會每個月有四次﹐兩次是在媛姐的家舉行﹐都在上午。孩子出生前﹐她有時候去﹐孩子滿月后﹐她就常常去了﹐因為在坐月子期間﹐她發現天上真的憑空掉餡餅下來﹐還掉雞湯﹑魚湯﹑這樣補的菜﹑那樣養的方﹐等等﹐總之﹐本來無親無故的她發現上天突然賜給她不少姐妹——而且是經驗和愛心都很豐富的姐妹。她感動不已﹐所以孩子一滿月就以出席率來作為報答的方式之一﹐因而也有機會知道媛姐每年總有一兩次旅行﹐長年下來﹐已經是個買票的行家。她拜托媛姐替她買張到上海的機票﹐越快越好﹐票買到后她再給媛姐支票。
媛姐聽張莉這么急﹐嚇了一跳﹐以為她的家里出了不幸。張莉說﹕「沒有沒有﹐只是我想盡快離開美國而已。」
媛姐是張莉所信任的﹐所以知道一些他們夫妻的過節﹐就問她是不是同李岩吵架了﹐張莉說﹕「是。不過這是最後一架﹐以後不會再吵了。」
媛姐聽明白了﹐她和緩地問張莉﹕「你很委屈﹐受不了了﹐是不是﹖」
張莉說﹕「可能吧。」喉嚨卻發澀﹐「吧」字講完的時候﹐眼淚就掉下來了﹐怎么也忍不住。
「李岩知道你要回去嗎﹖」媛姐在那邊又問。
張莉已經無法回答﹐她的寧靜莫明奇妙全沒有了﹐空曠也沒有了﹐一顆心裡飽飽地含著不知從哪里跑來的該死的眼淚﹐她若是開口﹐就會大哭。
「張莉。」媛姐輕輕喚了一聲。
這邊張莉整個嘴唇和下巴都在抖。
「你是在家嗎﹖」媛姐輕輕問。
「是。」張莉說﹐哭腔已經非常明顯。
「你等我。我這就過來。啊。」媛姐說。
李岩在老梁的沙發上一點也沒有睡好﹐頭像塞了一些木宵﹐眼皮則外面重里面澀。其實老梁的沙發比他自己家的好﹐不僅大些﹐而且新些。可是不知道是很少有人用的原故﹐還是屋子通風太少﹐沙發上有一股奇怪的霉味﹐這股味道一但聞到了﹐好象就沾在他的鼻子上﹐他仰躺能聞到﹐側躺還是能聞到﹐讓他沒發安寧。唯一能擺脫它的辦法就是跟沙發不沾邊﹐可他睡哪兒呢﹖他原以為老梁這里是很理想的避難勝地﹐有地方﹐沒家屬﹐雖然有「修正案」﹐但修正案不會天天來﹐沒想到倒霉時遇到的沙發也是霉的。
老梁還在早晨黯灰的光中酣睡。這難怪﹐昨晚老梁可沒有少費口舌來勸他﹐還陪上好几瓶啤酒。這些啤酒﹐一部分進了廁所﹐還有一部分全擠在他的腦血管里﹐把他的頭脹得直痛。老梁昨晚講的話也有百分之九十九都隨廁所的那部分啤酒流走了﹐幸存那點「抨﹑抨﹑抨」地敲擊著他的腦殼﹕「你要是不回家﹐已經有的問題可能會加重﹔而且﹐還沒有出現的問題可能會出現。」
這句話為什么會留下來﹐李岩不知道﹐也不想去理會﹐他只知道他心中有一口氣要同這世界爭﹐同張莉爭。會有什么問題老梁昨夜也沒有說﹐覺得李岩自己會去想。李岩的英雄氣被兒女情擠歪了鼻子﹐他才不要去想﹐也不要回去﹐只要求老梁在他落難時多收留他幾天。老梁把該說的話說完了﹐就把一把鑰匙給了他。生活畢竟是每個人自己的﹐何況他自己也不是一個婚姻的行家﹐只是有了兒子做壓艙石﹐婚姻的船一時顛覆不了。現在朋友的婚姻遇到了壞天氣﹐他又沒有改變天氣的翻雲複雨手﹐能幫到哪兒就幫到哪兒吧。老梁盡完義務后就安枕而眠。
沒驚動酣睡中的老梁﹐李岩早早出了門﹐去學校。
這是個清冷的早晨﹐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毛毛雨﹐雖然已經有不少人來來往往﹐但還是清冷的很。
草早就綠了﹐路邊的草坪都頂著密麻麻細淬的露珠﹔樹卻還沒有新芽。這是個春季和冬季并存的地方。一只松鼠不介意這毛毛雨﹐蓬松的大尾巴一抖﹑一抖地在濕黑的樹枝上邊吃早餐邊看行人。李岩從它的樹下走過﹐不知是不是這個早晨的清冷浸進了他缺乏睡眠的頭﹐他頭中的木屑都沒有了﹐但他既沒有看見草地上清新的綠﹐也沒有看見針葉樹陳舊的綠﹐他心裡只衍生著一種輕如鴻毛的感覺﹐就算他的夜晚和心情如何地驚天動地﹐這個世界卻對他不會不多看一眼﹐他有沒有在這個早晨在這里行走﹐對任何人﹑任何事都毫無分別。
李岩到達公車站的時候﹐毛毛雨突然大起來﹐他正待要躲雨﹐卻看見公車從那邊準時來了﹐所以就在原地等﹐結果﹐等他人上了車﹐衣服也濕透了。
到了實研室﹐身上粘乎乎﹑濕答答地不舒服。不久﹐體胖心善的技術員麗莎也來了﹐看他難受﹐不知從哪里找來的一個吹風機給他用。他正用吹風機上下吹干自己﹐誰知把老板也吹來了。老板年過半百﹐肩寬體壯﹐臉上沒有眼鏡﹐腰上也無幅度﹙福肚﹚﹐高興時眼睛放光﹐不高興時眼睛也放光﹐看上去讓人想到的是體育場而不是實研室。有他在旁邊一站﹐本來不高也不矮的李岩就立刻顯得瘦小﹐像白鵝旁邊的一只尷尬的濕公雞。老板一看明白他要看的﹐眼睛就發光﹐并沒有說什么﹐但象是什么都說了﹐吹風機在李岩的手上就再也呆不住。
午飯時間過后﹐李岩的衣服已經被體溫和室溫烘干了﹐可是頭卻加倍的昏沉。他自己用手試試額頭﹐火燙。
時間自此也像是被他的燒給嚇住了﹐一秒一秒過的分外遲疑。好容易熬到下午三點﹐麗莎注意到他的滿面紅光很不正常﹐這才力勸他回去休息﹐或是去看看醫生﹐還堅持將傘借給他﹐囑咐他不能再琳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