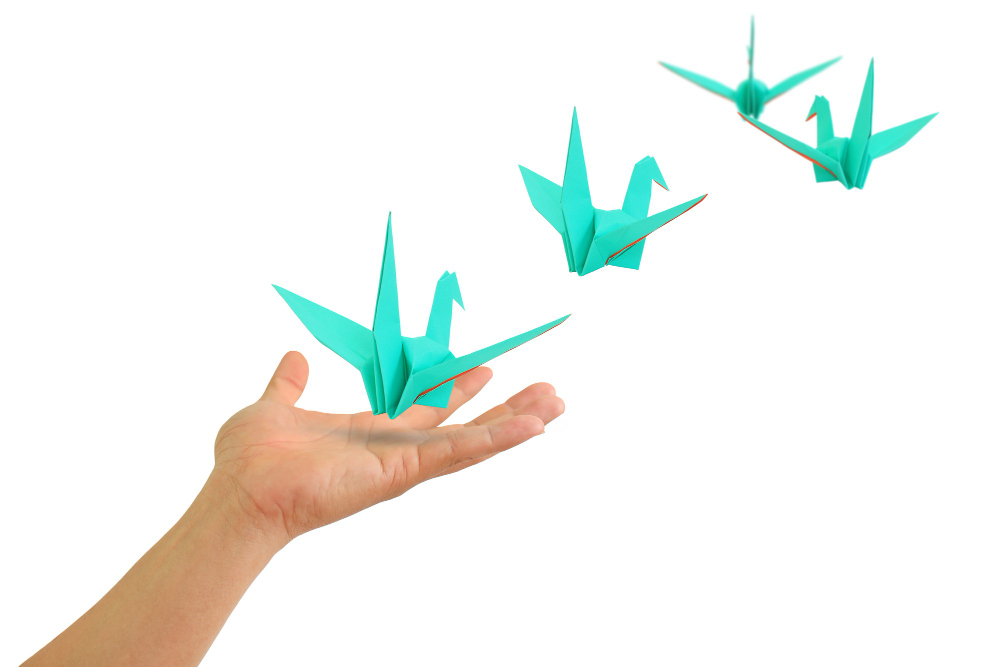
文/ 李文屏
三 冷夜冷戰
她知道她今天是殘酷的﹐雖然是因為被踩痛了﹐反勾了他一腳。噯﹐夫妻要傷害對方還不容易嗎﹖天天見面﹐機會多的是﹔心肝肺腑都敞著﹐要傷有多重﹐傷就能有多重。
浩蕩的海風從太平洋橫掃到李岩的臉上﹐齊秦悲壙的歌聲響在他的心中﹕
「我是一只來自北方的狼﹐
走在無際的曠野中﹐
淒厲的北風吹過﹐
漫漫的黃沙掠過……」
海風把他的頭發齊根掀起﹐呼拉拉往後折﹐露出額頭來﹐張莉要是在情緒正常的情況下見到他這個樣子﹐恐怕會嘻誇他原來也有几分軒昂之氣﹐可惜被他不肯修的邊服給抹殺了。李岩看不到自己的樣子﹐路燈下倒是看到迎面來的一個男子﹐上身腫﹐下身細﹐如果不是多長了一個頭﹐就像一朵腿長的磨菇。這顆頭在這個大風的夜晚也顯得奇怪﹐頭髮像黑布片一樣被風全趕往臉上﹐一撲一撲的﹐仿弗只有了鼻子和下巴的臉就在黑布片中間忽閃忽閃。
李岩沒有理由地厭煩這個有些狼狽的形象﹐它瑣宵地闖入了他悲壯的曠野﹐又似乎是他生活的寫照﹐被張莉用她的伶牙利齒從虛空中招將過來給他看。
他把眼光趕快直直地投到前面去。他實在不認識今天的張莉﹐因為張莉婚前是個溫柔的大女孩﹐婚后是個溫柔的小女人﹐很少在言語上與他真刀真槍地贛仗。可這丫頭今天不知吃錯了什么藥﹐嘴皮子變得跟北京公共汽車上的售票員也差不多了﹐損起人來「有理有節」﹑還一個臟字也不帶﹐把個人要活活堵死。
「嗨﹐李岩﹐這么晚了還出來散步啊﹖」他的生活寫照卻開口同他寒喧﹐并用手往外清理臉上的頭髮。
李岩吃了一驚﹐想不到是個熟人﹐而且是幾個小時前剛見的熟人。
「哦﹐老梁啊。剛回來﹖」
只怪燈太暗﹐風太大﹐讓有模有樣的老梁變了形。
「剛回來。還是年輕好啊﹐看看你﹐穿得這么單薄就出來了。這天氣變得好快﹐出去時還好好的。」老梁說著﹐用手去抱自己黑夾克裹著的身子﹐磨菇立刻變了形﹐頭髮也馬上撲回他的臉上。
「是有點冷。剛才家里熱﹐所以不知道外面這么個天氣。」李岩胡亂應對著。
「家里熱﹐家里當然熱啦。理解理解。」老梁說﹐把個熱字說得格外意味深長﹐「不過﹐再熱﹐出門來還是要加件外套。」
李岩也不在意﹐老梁剛「熱」回來﹐什么都還帶著「熱」的溫度。
「回頭見啊。」老梁對李岩擠擠眼﹐讓風把自己吹走了。
李岩突然覺得有大風好啊﹐好讓他可以被吹得清醒一些。
以前他對老梁的本行理論并不很以為然﹐甚至對飯桌上談這樣的話題感到不太自在﹐有點穿睡衣走大街的感覺﹐當然﹐不喜歡穿睡衣到大街上﹐不等於說他在該穿睡衣時不喜歡穿。可今天﹐他被老婆氣出家門﹐而就在這時﹐老梁﹐有理論有行動有快樂的老梁與他擦肩而過﹐不就是要提醒他﹐他雖然年輕﹐但已經迂腐﹑過時了嗎﹖他不僅趕不上時代﹐尤其是美國的時代﹐更趕不上生活自己。同樣是來美國洋插隊﹐同樣是天涯奮鬥客﹐老梁卻是自在的﹐老梁是他自己的主人﹔而他呢﹖受學業的氣﹐受老板的氣﹐還要受由他養活的老婆的氣。他真實窩囊啊。
可他為什么要趕什么時代呢﹖他就是他﹐時代若是在他的專業之外就與他沒有關系﹔若不是張莉氣他﹐時代是在他前面還是在他後面也與他無關﹐他不會在大風天因為時代而出來「散步」﹐就像他不會為了時代去剪一個時代的髮型。
當然﹐他也沒有在婚后為張莉剪過頭髮﹐也許在潛意識里﹐他知道張莉和時代是穿同一條褲子的﹐男人如果在外面得不到社會認同﹐在家里怎能得到老婆的尊重﹖他既然不宵於取悅時代﹐也就不宵於取悅張莉。以前他以為張莉不俗﹐跟一般的女性不一樣﹐今天才知道她不俗是因為她沒有機會俗。那時他一切都順利﹐張莉哪里有機會顯出「俗」來呢﹖可今天﹐她的俗樣全露出來了﹐她不是也嫌棄他不能乾了嗎﹖如果他是個成功的人﹐她會這樣對他﹖她以前對他多好啊﹐哪里會在他哪里痛就往哪里戳。話說回來﹐他要是一切都順利﹐有痛處讓張莉這丫頭來戳嗎﹖
好冷。
冷風已經吹透他的并不結實的肌肉﹐滲進了內臟和骨髓。除了偶有一兩個用功晚歸的人從夜色中匆匆走過外﹐冷風似乎吹走和正在吹走地上的一切。天上倒有不少寒星﹐冷漠高遠地亮著。
他又繼續走了一程﹐覺得身體的里里外外都是風﹐冷得受不了了。
他頹然反身。風攜帶著一撥落葉和雜物「嘩嘩嘩」地從他腳前跑過﹐一個脹了一肚子氣的塑料袋在半空翻跟斗﹐跌跌撞撞地也過去了﹐消失在前面的黑里。他跨過一條被風吹落又遺棄的斷枝﹐往他出來的地方去﹐往那個不再看得起他的那個女人那里去﹐心裡覺得窩囊和空茫﹐不知道要如何與她面對。
奇怪以前他怎么不知道她的口才這么好﹖是啦﹐以前他有這么倒霉嗎﹖日久見人心啊﹐患難現虛情。回去就倒頭睡吧﹐他媽的睡沙發。都說男女是因誤會而結合﹐因了解而分手。也許﹐他跟張莉越來越了解了。哈哈哈。
公寓的床上﹐張莉本來在流淚﹐突然她的身體一僵﹐眼淚也不流了。自李岩一走﹐屋子就靜了下來﹐太靜了﹐她一直聽到冬風從屋頂和窗前跑過﹐像一群接一群呼號的狼魂﹐為她悲傷的心情作背景﹐直到聽久了﹐這背景配樂才跑進意識的前臺﹐她突然想起李岩就是在這樣的大風里。
她起身跑到客廳去﹐果然李岩的冬衣還慫拉在沙發上。這個笨人啊﹐出去就出去﹐為什么不把衣服穿上。
她把門打開一個縫﹐冷風蛇群一樣忽攸就躥了進來﹐飛起她的頭髮﹐立馬給她一個透心涼。她聳著薄薄的肩膀﹐趕緊把門合上。這個人一定是瘋了﹐在外面凍了半天還不知道回轉。天地良心﹐她不想傷他﹐不想去揭他的痛處的﹐可是她恰恰做了她不想做的事﹐而且是故意做的。她氣跑了他﹐哪里又有得勝的喜悅。她的心跟他一樣痛。夫妻打架﹐手上拿得不都是兩頭尖的劍嗎﹐傷了對方怎能不傷自己﹖他們這是做什么呢﹖越是夫妻兩個該好好互相扶助的時候﹐越是互相拆臺。
張莉一手拿起李岩的外套﹐想出去找他﹐可是孩子怎么辦﹖總不能把孩子一個人留在家中吧。誰知李岩跑到哪里去了﹖
她走到窗前﹐揭開窗廉﹐外面﹐風搖憾著黑漆漆的大樹﹐對面公寓樓的昏暗路燈在搖撼的枝葉中忽閃忽現。
他應該不會在外面呆太久吧。
張莉在臥室呆一呆﹐在沙發上坐一坐﹐又隨手拿起一本不知哪里來的《國家地理雜志》來翻﹐又把雜志扔到茶幾上。這樣徘徊往來﹐當她目光再次落到雜志上時﹐封面上一直在亮相的北極熊終於被她看到了。
「他不會像北極熊一樣經凍的﹐」她想﹐「而且這么晚了﹐也不能去誰的家。他應該很快就會回來的。」她力圖說服自己。
李岩本來是該到家了﹐可是在回程中﹐恰巧經過他今天用過的自習室﹐突然想起自習室是通霄開放的﹐不由心里一寬﹕阿弥陀佛﹐不需要馬上回去見那個女人啦。
手抖著﹐李岩從自習室外面的布告欄取下一張紙來做自習的道具。他不能兩手空空地去自習室自習吧。
手不太聽使喚﹐紙被取下來了﹐又掉在地上﹐風一下子就把它卷跑了。李岩暗罵一聲﹐突然怒發沖冠﹐以不顧死活的架式「唰」地一聲連撕帶扯弄下另外一張什么東西﹐用牙齒咬住﹐手抖抖嗦嗦從褲包里摸出冰涼的一串鑰匙﹐然後歪著脖子抖了半天找到正確的那把﹐又抖了好一會兒才把鑰匙放進鑰匙孔中。
自習室的熱氣迎面撲到臉上﹐他全身的皮膚細胞如同久旱垂死的魚群又落進水里﹐大口大口﹑迫不及待地吞吸著室內的暖空氣。
像是感覺到教室里的熱空氣突然被吸走了﹐一個女學生抬頭來看李岩﹐露出驚訝﹑關切和害怕的表情。李岩當然沒有看見﹐因為自習室已經一片模糊﹐熱氣早將他的兩個鏡片變成了兩個白色的眼罩。
他笨拙地摘下近視眼鏡﹐在矇朧中看到自習室里還坐著三個人形的東西﹐也分不出男女﹐總之都是死人﹐都聽不到門口想進來的人半天打不開門﹐竟然沒有一個來給他開門的。
他找到一個角落坐下﹐將從布告欄掠來的「道具」攤在桌上﹐靜靜地發呆﹐對「溫暖」這個用爛了的詞義有了徹底的懂得。他閉著眼睛沉浸在他新找到﹑新懂得的溫暖里﹐沒有注意到有兩個女生已經怕怕地離去﹐剩下一個男生又警惕又關切地在打量他。李岩旁若無人﹐他想﹐這個世界哪怕再冷﹐可是如果那個叫做家的小窩有溫暖﹐人就凍不死﹐就可以活得下去。
可是他的家呢﹖
想到家他就想到張莉﹐他很快就意識到這一點﹐而且也咬牙痛恨這一點。怎么家跟女人這么休戚相關﹖那個老梁有了婚外情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老婆那么遠﹐他孤伶伶一個人﹐白天在事業上拼命﹐晚上回家冷冷清清﹐不想溫暖才怪。有愛的女人本身就是溫暖﹐所以老梁在美國有了一個愛他的女人。老梁的老婆還愛不愛老梁他不知道﹐就算還愛﹐可這個愛遠在天邊﹐等輻射到老梁身上﹐恐怕也跟今晚那天上的星星一樣﹐有光無熱了。他和張莉的兒子才四個月﹐他已經開始離家出走了——雖然是超短期的﹐他知道他坐一坐還是要回去的——而老梁夫妻的兒子都十歲多了﹐中間已經有過多少架﹐多少次出走——實際的或者心裡的﹐就不好說了。他和張莉這樣下去﹐就是不離婚﹐等他們的兒子也十歲的時候﹐他會不會有婚外情真是不敢擔保。如果說張莉曾是他的溫暖的話﹐這個「溫暖」今天差點沒把他凍死。
手指已經靈活了一點﹐他開始用衣角擦拭鏡片﹐越擦越快。
「你需不需要把暖氣再開大一點﹖」
他突然聽到有聲音在問﹐抬起頭﹐看到一個人形站在門口。模糊的視野里并沒有其它的人形。是問他嗎﹖
他戴上眼鏡﹐看清門口背著書包﹑像是要走的男生果然在看著他﹐并又重複問了一遍﹐同時用手指指牆上的暖氣調控板。
李岩哦了一聲﹐點點頭表示知道了。男生就開門走了﹐剩他一個人在教室里枯坐。
張莉在家中也黯然地坐著。兒子已經申請「開飯」了﹐所以她一邊奶孩子﹐一邊聽外面的風嘯。李岩這個臭東西﹐不會照顧老婆和孩子﹐總該會照顧自己吧。她想起她的基督徒朋友們討論過什么是愛的問題﹐模糊記得有一句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的話。愛是不是一定要恆久忍耐﹐她覺得未必是這樣﹐對於惡行要恆久忍耐嗎﹖可是﹐愛中要有恩慈﹐她倒是滿同意。這使她感到難過﹐為李岩﹐也為她自己。歷史問題就不談了﹐就今天而言﹐李岩對她沒有恩慈﹐更沒有懂得和體諒﹐所以才在言語態度上踩她。
而她呢﹖
她知道她今天是殘酷的﹐雖然是因為被踩痛了﹐反勾了他一腳。噯﹐夫妻要傷害對方還不容易嗎﹖天天見面﹐機會多的是﹔心肝肺腑都敞著﹐要傷有多重﹐傷就能有多重。她真的不應該這樣對李岩﹐盡管李岩也不該那樣來對她。
不知過了多久﹐張莉聽到門鎖的聲音﹐她攸忽醒來﹐才知道自己不知什么時候已經在臥室的床上睡著了。
客廳的燈還開著﹐李岩的腳步慢吞吞往這邊過來。張莉擔心他是不是凍壞了﹐她聽到自己在問昏暗的天花板﹕「你還好吧﹖」聲音比她的心枯干一百倍。
李岩沒有吭聲﹐他不要理這樣的虛情假意。他就是凍死了﹐她一樣在家睡熱被。他胡亂找了一床薄被就返回到客廳﹐啪的一聲關了燈。張莉眼前一暗﹐然後聽到買來時就很舊的沙發在黑暗中一陣響。
睡沙發了﹖
這張莉倒沒有想到。她突然覺得自己傻﹐自己天真。她在為他心軟呢﹐他卻決然與她疏離。什么恆久忍耐﹗她對他忍得夠多了﹐所以才將他縱容成這個樣子﹐只能他傲慢傷人﹐她不過是回傲他几句﹐他就受不了了﹐難倒他們婚姻的和平是建立在她對他單方面的忍耐上﹖
長此以往﹐國將不國﹗
張莉掀被起身﹐「啪」地將臥室的門插上了。
風還在外面狂吹﹐張莉覺得自己似乎也聽到李岩在外屋狂笑。
不管李岩和張莉的冷戰要怎么打﹐他們的兒子并不體諒戰事激烈﹐還是到點就要求開飯。張莉聽到兒子的哭聲﹐她不動﹐忍了几秒鐘﹐并沒有聽到李岩起身的動靜。她忍不了了﹐在兒子的問題上與他鬥氣﹐她永遠會是輸家。斷奶吧﹐斷奶她就可以將兒子托給別人帶﹐她就可以重新走向世界﹐不在家受李岩的氣﹔不斷奶兒子就只是她的﹐也只有兒子是她的﹐李岩正離她而去﹐而且樂得什么也不管﹐只管說風涼話。
張莉打開臥室的門﹐出去照看兒子﹐喂奶﹑換尿布﹑拍奶﹐換兒子吐奶吐濕的衣服。什么是愛﹐這半夜起床喂奶﹑換尿布﹑拍奶﹐換兒子吐奶吐濕的衣服就是愛﹐李岩體貼她辛苦她會這樣做﹐李岩不體貼她她也會這樣做﹐她不能因為丈夫不象話就改變初衷﹐她不能。可是﹐如果李岩體貼﹐她心裡的感受會如何不同啊。
兒子飽足﹑乾淨之後﹐在張莉的懷里安然入睡了﹐張莉將自己的頭埋在孩子的小被子上面很久﹐很久﹐兒子的體溫從被子下面透過來﹐捂著張莉淚濕的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