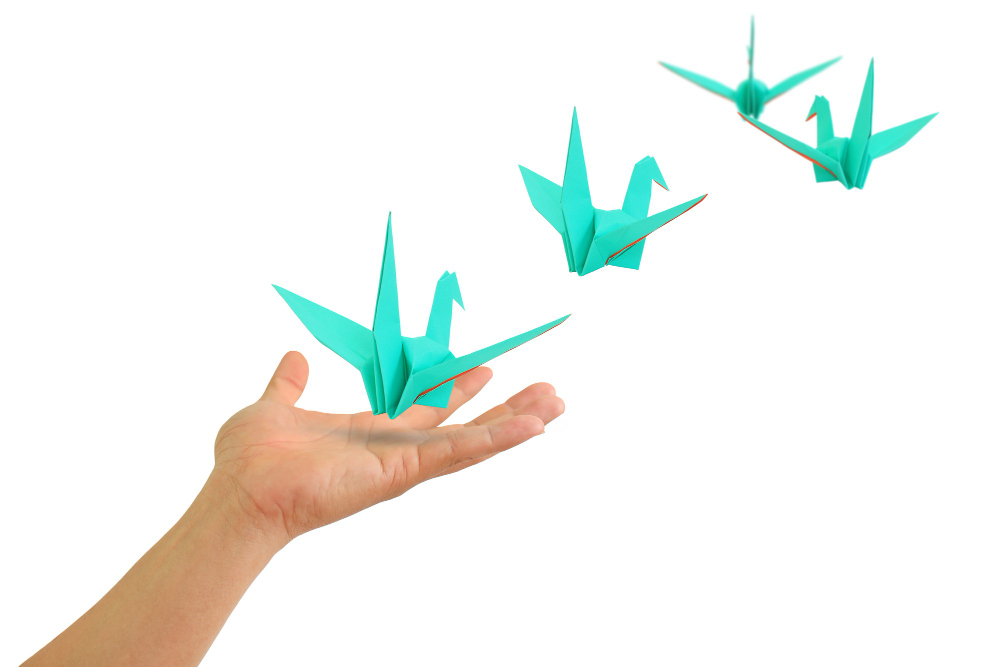
文/ 李文屏
二 悲傷什麼呢? 不是贏了嗎?
李岩被她噎得發昏﹐腦袋里應對的詞兒全沒了﹐只有几股氣流在身體里亂躥﹐卻不能躥到手掌上去打老婆﹐這有違他的大男人風范﹔也不能躥到頭上去撞牆﹐這是弱女子才有的形象﹔所以只得躥到腳上。他一轉身打開廚房的門﹐又「砰」的一聲關上﹐一頭撲進黑夜里。那「砰」的一聲﹐是門替他做的嚎叫。
大家坐定。平時生活忙碌﹐這總統節﹐長周末﹐雖然是光明正大的假日﹐空氣中卻洋溢著一種偷閑的快樂﹐仿弗他們是從時間這個吝嗇的老板那兒突然賺了一把回來。
沒人懂得老梁為什么要突然帶凱娣來到他們中間。大家是第一次與她見面﹐因對她的身分心照不宣﹐在要開口寒喧的那一瞬間又突然明白寒喧其實叫做問長問短﹐似乎不太合適﹐所以沒人多嘴與她說話﹐只是一與凱娣的目光相對﹐就趕緊堆出笑來。
所以大家自始至終都不知道凱娣是在做事還是在做學生﹐是東南亞來的華僑後代﹐還是美國生或美國長的黃香蕉﹙外黃里白﹚﹐芳齡几許﹐家在何處﹐與老梁怎么認識的﹐怎么被老梁弄到手的﹐知不知道老梁有了老婆了﹐等等。這些問題在大家的腸子里百轉千折﹐自生但不自滅﹐被成功地壓制在禮節和友善中。
在大家的想當然里﹐老梁的修正案應該是個﹑或者是些滿開放的女人﹐沒有想到這個凱娣一見之下卻是禮服里面的一朵菊花﹐很有些個純朴羞赦之氣﹐雖然看起來二十四五了﹐可一笑就把歲數減了個七八年。所以七點半老梁攜凱娣一走﹐汪太太就說﹕「這個凱娣也不知道到底多大了。第一眼看覺得她跟張莉差不多大﹐可是﹐越看好像越小。」
張莉想起凱娣看老梁時滿足和依戀的神情﹐臃懶地感嘆地說﹕「她看起來對老梁蠻痴情的。」邊說邊往椅背上靠﹐將剛才幫忙做事時挽上去的頭髮放下來﹐讓它們在椅子後面垂下﹐然後伸出一只穿白襪子的腳去搖身邊的籃子。籃子是嬰兒在車上用的座位﹐里面躺著他們四個月大的兒子﹐摸樣已經明顯了﹐像他媽﹐白白淨淨的﹐長眼睫毛﹐此時剛醒來﹐嘴巴一咧一咧﹐仿弗要哭﹐但還沒有哭出來就給籃子搖下去了。
「她痴她的情﹐你感嘆什么﹖」汪太太說。
張莉笑﹐說﹕「我想起丘比特來了。」
「丘比特﹖那個天使啊﹖」汪太太說。
「對呀。那個傳說中的愛情天使。你不覺得奇怪嗎﹖丘比特管的是成年人的事﹐但他自己是個才几歲的小娃娃﹐射箭的時候還蒙著眼睛。」張莉說﹐感嘆凱娣﹐也隱隱約約地感嘆自己。
她還沒有忘記李岩和她的好時光﹐也許正因為如此﹐現在的李岩和過去的李岩就有了對比和反差。有些小事就不挑剃了﹐比如說他再沒有給她夾過菜﹐仿弗那是戀愛期和蜜月期的突發技能﹐像個夢中的奇跡﹐現在夢醒了﹐它就跟夢一起煙消雲散了﹔再有就是一起出門﹐李岩也得了健忘症一樣常常忘記他的力氣比她的大﹐她沒有請他幫忙提東西﹑提兒子﹐他就常常想不起來要幫忙。他也很少看得見她為他和這個家所做的﹐覺得他太辛苦﹐她則無所事事﹐在家享福﹐好象他是生活在全自動的未來世界里﹐不僅所有的衣服都會自己清洗自己﹑自己疊好自己再自己躺進他的衣服抽屜里﹔飯菜也是到點就自己清洗﹑入鍋﹑加味﹑裝盤﹔家里的塵渣自動離開﹑屋件自動到位﹑廁所自動乾淨﹔甚至他們的兒子的尿布也是每隔兩三個小時就自動脫落﹑更換﹐兒子一餓﹐有一個飯店白天數次﹑晚上數次自動為他開張營業﹐營業內容包括喂到兒子嘴里和喂完后拍奶﹔諸如此類吧﹐真正讓她難過的還是大事﹐是一些原則問題。
學業上沒有聽說在柏克萊讀博士很容易的﹐這跟托福和GRE的高分沒有太大關系﹐那么學業不順怎么能說是因為她要他陪的時間太多了呢﹖沒有她他就不花時間吃飯了嗎﹖沒有她他就不花時間洗澡了嗎﹖真正花在她身上的時間其實差不多就只有夫妻的事了﹐夫妻的事上到底是誰陪誰呢﹖這哪里是個誰陪誰的問題﹖何況真正在美國陪上時間和青春的是她而不是他﹐是她放棄職業的夢想﹐失去許多不該失去的尊重﹐在家做主婦﹐天天做那些做了就像沒有做的事。就是女佣你也得說上几句話不是嗎﹖何況是你的妻子呢。她難過的還不僅是這個問題的本身﹐更難過的是她看到他正在失去舊有的男子氣概﹐這樣怪老婆的人你能說他有男子氣概嗎﹖
還有﹐老板對他凶﹐那個老板對哪個外國學生是客氣的﹖老板自私﹑修養不好跟她有什么關系﹐可是李岩說他是為了她才到美國來受這個洋罪的﹐言下之意她是他受洋罪的根源。她沒有叫他來美國﹐他來了之後﹐她放棄了國內的發展前途來陪他﹐可是她成了他受罪的原因。何必把自己的求學動機抬得這么高尚呢﹐為了自己的發展前途來求學并不壞﹐有什么必要要把自己當成崇高愛情的犧牲品﹖
起初﹐她體諒他壓力太重﹐把她這個異國他鄉里唯一的自己人當作自己人來撒撒氣﹐所以就忍忍算了。可是時間長了﹐事情累積下來﹐心裡難免委屈﹐加上在家帶孩子的生活繁重瑣碎和封閉﹐況且﹐不只是他﹐她也是在異國他鄉啊﹐所以他越來越成為那個唯一可以相依的「命」﹐對他的期望的結果卻常常是失望。一個不斷失望的妻子﹐要保持對丈夫原有的愛﹐容易嗎﹖幸好有些朋友來往相勸﹐尤其是那幾個基督徒朋友﹐很會用話語來解開人心裡的疙瘩﹐也舍得花時間來與她相處﹐所以她也去教會﹐也花時間去了解《聖經》﹐也信了基督﹐結果卻是讓李岩多有了一個原因來小看她。
兩個女人談話的時候﹐兩個先生都有一副淡遠無關的樣子﹐好象沒有見過凱娣其人。
汪太太說﹕「我看丘比特雖然瞎至少射對了一次﹐要不你們倆怎么會湊到一起﹐是不是李岩﹖你太太多溫柔啊﹐又好看﹐我都沒有見她聲音大過。李岩的脾氣也好。你們倆吵過架嗎﹖誰聽誰的呀﹖」
李岩笑﹐食指把鼻梁上的眼鏡一推﹐借用不知在哪里見過的一則笑話說﹕「我們家是民主政治。意見相同時張莉聽我的﹔意見不同時﹐我聽張莉的。」
汪澎挺著肚子笑﹐眼睛又變成一條縫﹔汪太太沖著張莉擠眉弄眼﹐用手遮著嘴巴﹐因為嘴里正有一口菜﹔張莉則牽著嘴角笑﹐心裡覺得與事實有出入﹐不過她沒有說什么﹐隨李岩張揚自己的幽默和大度。畢竟這是個不錯的玩笑。
這樣東拉西扯到了九點﹐賺來的「閑」就這樣花完了﹐時間的重手又開始按在李岩的肩膀上——他還有不少該讀的資料沒有讀——所以李岩夫婦也告辭了﹐而且一到家李岩就背上書包去了自習室。
李岩自習回來時已經快一點了﹐頭昏心煩﹐見張莉還在臥室讀《聖經》就說﹕「累的累死﹐閑的閑死。這麼晚了﹐怎么還不睡﹐到時候又說睡眠不足。」說著﹐將書包往地上一扔﹐嘆氣﹐一頭倒在床上。
張莉本來想解釋說﹐她剛忙完不久﹐馬上要到孩子醒來吃東西的時間了﹐所以乾脆讀點書﹐等一會喂完了孩子再睡﹐也容易睡著。但聽李岩的話不入耳﹐就不吭聲﹐也不動。
「聽見了沒有﹐早點關燈睡覺。」李岩對張莉的沉默來火。
張莉說﹕「累了﹐睡不著。」
「不睡怎么能夠睡得著﹖再說可以讀的東西多了﹐讀那個東西乾什么﹖浪費時間。」李岩鄙夷地在鼻子里面哼了一下﹐起來去了廁所。
張莉發現他的語氣很討厭﹐本來還中看的臉因為鄙夷而實在扎眼。她沒有吭聲﹐起身去了客廳。
李岩從廁所出來﹐看見張莉雖然換了地方﹐卻還是抱著《聖經》在看﹐心裡更無名地煩。
「我說張莉﹐你還真的信那個玩意﹖你也是受過大學教育的﹐怎么會淪落到這個地步﹖」
「你要我替你做什么嗎﹖」張莉答非所問。
「我不要你為我作什么﹐我要你休息。」
「我就是在休息。」
「這不是休息﹐是迷信。」
「就算這是迷信﹐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是在休息。」
「你也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知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休息﹖」
「這就對了﹐我不知道你﹐但我知道我自己。我知道這樣我是在休息。」
「你知道什么﹖你不要老是跟那些迷信的人來往。愚昧的人才迷信這玩意兒。」
張莉聽不下去了﹐尤其是第一句「你知道什么」。在家不上班就什么也不知道﹖﹗什么話﹗還是國內的朋友有遠見﹐知道她舍不得送孩子回國﹐要自己在家里帶孩子時就勸她說﹐女人不能沒有自己的事業﹐否則就是你為了愛情和家庭當牛做馬﹐他也不會很珍惜你﹑很尊重你的。誰會珍重牛和馬呢﹖果不其然﹐看看李岩這副張揚的德性。自從她到美國來作賢妻良母﹐李岩對她是一天不如一天。
她把書一合﹐本來就白的臉更白了﹐冷冷地笑說﹕「我有點奇怪﹐她們這些愚昧的人勸我說﹐丈夫是妻子的頭﹐作妻子的要順服丈夫。您這個有知識不愚昧的博士﹐怎么也要我聽你的﹐包括什么叫做我的休息。您怎么跟她們一個調調呢﹖難倒您﹐也愚昧﹖」
李岩感覺喉嚨一堵﹐「你「您」啊「您」的乾什么﹖好心勸你休息﹐倒成了愚昧了﹖」
「您怎么會愚昧呢﹖您又不是在家帶孩子的家庭主婦﹐是博士﹐而且是美國柏克萊加大的博士——當然﹐博士學位還沒有拿到手﹐不過那也只是或遲或早的事——現在雖然書念得有點辛苦﹐可是都是因為有個笨老婆要陪﹐占去了太多時間的緣故。而且老板也是個笨蛋﹐狗眼看人低﹐受不了您的聰明和才華﹐所以您才虎落平陽被犬欺。現在您一片好心﹐要給您的笨老婆一些啟蒙教育﹐告訴她什么才叫做休息﹐可是她白痴一個﹐忘記了您就是真理﹐跟黨一樣偉大﹑光榮和正確﹐竟然敢與您意見不同﹐好象她也懂一點什么似的。真是對不起了。」
李岩被她噎得發昏﹐腦袋里應對的詞兒全沒了﹐只有几股氣流在身體里亂躥﹐卻不能躥到手掌上去打老婆﹐這有違他的大男人風范﹔也不能躥到頭上去撞牆﹐這是弱女子才有的形象﹔所以只得躥到腳上。他一轉身打開廚房的門﹐又「砰」的一聲關上﹐一頭撲進黑夜里。那「砰」的一聲﹐是門替他做的嚎叫。
張莉的眼淚聞聲流了下來﹐兒子也在里屋「哇」地一聲開始大哭。
「好﹐你走吧﹗你走﹗你走了就不要回來﹗」張莉在心裡大喊﹐想象自己跑到門口去將門一下子鎖死了。但現實中﹐她流淚跑進孩子的房間﹐安慰好兒子后又去臥室趴在床上哭。她的悲傷比憤怒更強。
悲傷什么呢﹖不是贏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