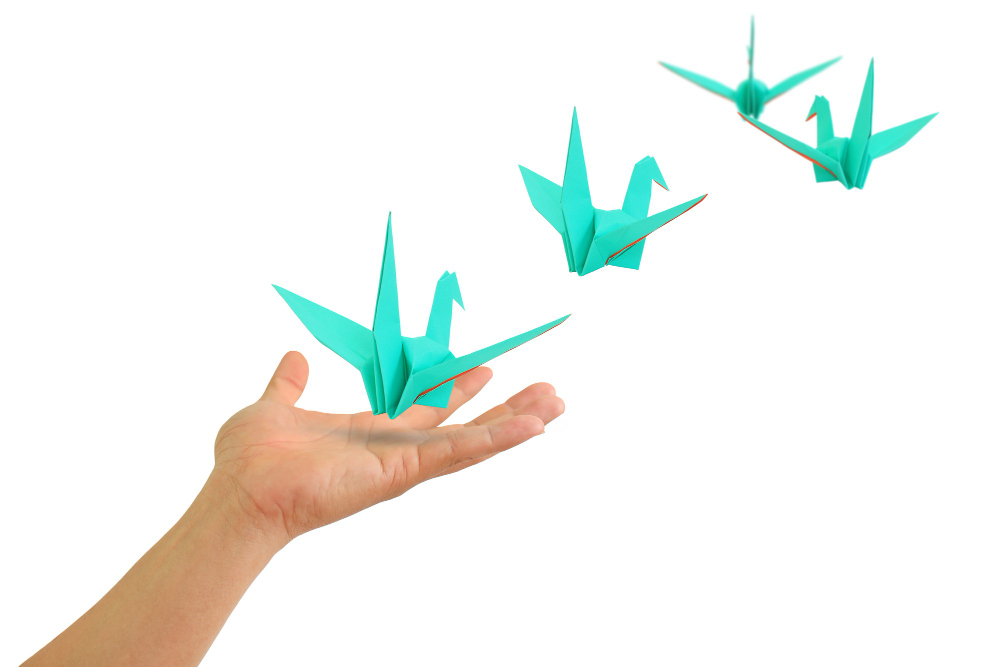
文/ 李文屏
五 「輪著糊涂」
如果等一百年你也還是要回去﹐那么等幾天也就無所謂了。幾天的時間不會改變一百年也改不了事﹐不過幾天時間也許可以讓你明白你是不是真的冷靜。
李岩在實研室吹干自己的時候﹐一個穿淡黃色雨衣的人揭開頭上的雨衣帽﹐路出卷曲齊肩的頭髮﹐黑中雜著灰和白。她敲響了他家的門﹐張莉開門﹐對著來者叫了一聲「媛姐」。
媛姐是要上門來做吹風機為他的太太吹濕透的心。
雨要下透了﹐天才放晴﹐媛姐明白這個道理﹐讓張莉在她的肩上哭個痛快。張莉哭完了﹐但并不痛快﹐一是哭得壓抑﹐怕吵醒兒子﹔二是哭雖哭完了﹐但心頭的烏雲卻沒完。
媛姐了解了事情的前後經過。
張莉說﹔「我受夠了。我要是回去﹐我媽可以幫忙照顧孩子﹐我也可以既有我自己的生活﹐也天天與孩子相處。何必在美國讓人小瞧呢﹐還被人拋棄呢——他不是出走了嗎﹖他以為就只有他會出走﹐我就不會出走﹗﹖我要走得更遠﹗他不要這個家了﹐我就一定要要嗎﹖我才沒有這么下作呢﹐憑什么要在這里過一種在社會上沒有前途﹑在家里也沒有前途的生活﹖李岩說他在外面吃憋﹐我則在家里吃憋的憋。我真的受夠了。」
媛姐很理解地點點頭﹐張莉以為媛姐贊同她的決定﹐誰知媛姐開口卻說﹕「是啊﹐我理解。不過﹐如果只是圖一時的痛快的話﹐回去的確是一個不錯的決定﹔但如果要解決問題﹐恐怕就不一定了。假如要問一個人憑什么明知受委屈但還是選擇受委屈的話﹐憑的就不是其它什么﹐憑得就只是愛。」
張莉瞪著媛姐。
她知道她聽懂了﹐但是她也沒有聽懂。有沒有搞錯﹐難倒媛姐要她以愛的名義去低三下四﹖這樣低三下四是「愛」﹖
媛姐微微笑﹐卻改變了談話的方向﹐提到張莉氣走李岩前與李岩的對話﹐說﹕「你當時講那樣的話﹐其實你并不是真的想那樣講﹐對不對﹖」她問。
張莉點頭﹐用手揉眼皮。悶悶地哭了一場﹐她在李岩哪里受的氣像是被哭進了眼皮﹐脹得難受。
「我們人其實都是這樣﹐一沖動就會講一些﹑或做一些本來在冷靜的時候并不想說﹑也不想做的事。所以﹐在我們不冷靜的時候﹐最好不要做一些重大的決定﹐你說是不是﹖因為這時候做的決定不可靠﹐可能事後會後悔。」
張莉覺得預感到媛姐下面會說什么﹐但是也只有點頭。媛姐講得有道理。
果然媛姐說﹕「你看﹐你現在還很難過﹐心中還有許多情緒沒有得到理清﹐如果在這個時候決定買機票回國﹐會不會不太是時候﹖會不會是情緒沖動的結果﹖所以等幾天﹐給自己一些時間可以回頭來看一看﹐我想這至少不會有壞處。」
「就是等一百年我也還是要回去的。」張莉決然說。
「如果等一百年你也還是要回去﹐那么等幾天也就無所謂了。幾天的時間不會改變一百年也改不了事﹐不過幾天時間也許可以讓你明白你是不是真的冷靜。如果幾天之后你確定你作決定的時候是冷靜的﹐所做的決定是一個成熟的決定﹐是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到時候再買機票也不遲。不過如果你發現自己原來不冷靜﹐那么也還有機會避免後悔﹐免得生米做成了熟飯﹐造成更大的不方便。回國畢竟不是去超市﹐說走就走﹐說回就回的呀﹐你要是不是拿的綠卡的話﹐誰能保證你想回來的時候美國就一定給你簽證呢﹖中美關系總是怪怪的不穩定。」
張莉若有所思﹐雖然她并不認為自己是情緒化的。
媛姐說﹕「假設——我是說假設啊﹐當然這樣的可能性會很大——假設李岩會有所改變﹐你還一定要離開美國嗎﹖」
她會嗎﹖
「李岩這樣不回家﹐一定是有點氣糊涂了﹐在氣頭上就做糊涂事﹐就像你那天在氣頭上就說糊涂話。你那天其實并不是真的想講那些話﹐那么同樣的道理﹐李岩也未必就真的是不想回家﹐是不是﹖人都難免糊涂﹐不過夫妻呢﹐要緊的是當一個糊涂的時候﹐另一個要不糊涂﹐顧全大局。實在要想糊涂一下圖個痛快﹐也等糊涂的哪個清醒了再輪著來也不遲﹐是不是﹖危害不會太大。怕就怕兩個一起糊涂﹐賭氣﹐傷害了彼此的感情﹐越傷越厲害﹐結果最後到了不好挽回的地步。」
張莉覺得媛姐「輪著糊涂」的話好笑﹐近乎孩子氣﹐不過這樣孩子氣的關系中似乎也有一種深遠的可愛和可親觸動她的心。她緊繃繃的臉上出現了一些笑意。
媛姐又講了一個故事﹕
「我知道有一對恩愛夫妻﹐起初也是吵來吵去﹐吵到丈夫有了外遇﹐妻子呢﹐想殺了丈夫和他的情婦﹐然後再自殺。不過就在這個時候﹐有個基督徒遇到這個妻子﹐看到她的情況不對﹐就特別關懷她﹐最後還帶她信了耶穌基督。結果基督為人死在十字架上的大愛改變了這個妻子﹐并使她的心裡重新充滿真摯的愛﹐一種從神和聖經那里吸取了能力和智慧的愛。她就用這樣的愛重新去愛她的丈夫﹐你知道嗎﹐就是這樣的愛漸漸改善了他們的夫妻關系﹐因為他的丈夫也因此改變了。他們夫妻重歸舊好﹑甚至比舊好還好。」
媛姐停頓下來﹐接著又說﹕「因為﹐唯有真愛——沒有雜質﹑不講條件的愛——才是最有力量的。改善夫妻關系最好的辦法就是這樣的愛。只有這樣的愛才能讓夫妻滿頭白發的時候﹐不只是偕老﹐而是…而是還可以手牽手過馬路。」
媛姐的最後一句話像魔術﹐張莉覺得自己仿弗看到一對白髮蒼蒼的老人家正手牽手蹣跚地過馬路﹐妻子有几根發絲被風吹散了﹐在風中輕輕舞動。馬路兩旁紅的是楓葉﹐黃的是銀杏﹐一直延伸到遠處的藍天里﹐像兩行美好永恆的詩句﹐向世界講解他們的情愛。
她嘆了一口氣。她知道自己在聽一個童話﹐一個動聽的﹑美麗的﹑感人的童話﹐一個與她無關的別人的故事。她喜歡這樣的故事﹐她為這樣的故事感動﹐她可以永遠將這樣的故事聽下去﹐可是又怎么樣呢﹖恩愛夫妻多了﹐可是不恩愛的夫妻更多﹐不幸她是後者中的一員。如果媛姐有恩愛的故事來鼓勵她的話﹐她自己一定可以找到加倍多的怨恨故事來將這些鼓勵抵消。故事能說明什么呢﹖何況它是別人的﹐別人的故事再好﹐她的「經」還是她的「難念的經」。而且﹐她雖然信了耶穌基督﹐可《聖經》的話并不那么入她的耳﹐比如做妻子的要「順服丈夫」啦﹐還有哪個「恆久忍耐」的話什么的﹐這些都屬於那個妻子找到的「智慧和能力」﹖
所以她有些淡遠﹑戒備﹑甚至帶了一絲嘲諷地說﹕「我知道一點點聖經的教導﹐比如說做妻子的要順服丈夫﹐你說的這個妻子是不是就順服她的丈夫啊﹖」
她想﹐如果媛姐今天要來勸她做這樣的女人﹐她還是不要聽的好。她要再對李岩順服﹐李岩不僅是尾巴要翹到天上去﹐恐怕下巴也要翹到天上去了。
「是的﹐順服是她改變自己的其中一條。」媛姐安然地說。
「就是她的丈夫有了外遇﹐她也順著他﹐由他亂來﹖」張莉覺得難以致信。什么年代了﹗在什么地方﹙美國﹗﹗﹚﹗怎么還講這樣的話﹖﹗今天媛姐真的是要來勸她倒退百年千年去做封建時代的女人﹐就差明確地講三從四德了﹐她不能讓這樣的勸導繼續下去。
媛姐笑了﹐說﹕「妻子順服丈夫是聖經的教導沒有錯﹐但聖經不是只教導這一條﹐所以讀聖經的時候也不能只將其中的一條單獨拿出來。聖經教導妻子﹐也教導丈夫﹐比如丈夫要愛妻子﹐愛到為她舍命。聖經中有些話是單獨對妻子說的,有的是單獨對丈夫說的﹐也有既針對妻子﹑也針對丈夫的。你看這里﹐這里有專門對愛的說法。」
媛姐指給張莉看一處經文。她是有備而來﹐《聖經》就裝在她隨身的包里﹐而且聖經雖然是厚厚一本﹐她一翻就翻到了要找的地方。
張莉不太情願﹐但媛姐似乎不像她所防備的那么封建﹐所以就順著媛姐的手指看了過去﹕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哦﹐原來那句有關恆久忍耐的話就在這里。
「這恐怕不是人能做的。別說恆久忍耐了﹐他要是再這樣下去﹐我一天也不能忍。媛姐﹐你不覺得有時候忍耐就是對惡行的從容嗎﹖」
「所以我說讀聖經的經文不能只抽出其中一條來﹐而是要與其它的經文連在一起來看。比如﹐這里說要恆久忍耐的時候﹐不是說你就要被動地做人的鞋墊﹐隨便人踩﹐逆來順受。這里講的忍耐是一種出於恩慈的忍耐﹐而且這樣的忍耐是與後面「不喜歡不義」連在一起的…」
話到這里﹐張莉的兒子哭﹐張莉道歉了就趕緊去里間照顧兒子﹐媛姐也跟過去前前後後地幫忙﹐等兩人重新坐定﹐媛姐說﹕「你的孩子還小。假設他長大一些了﹐會做一些你不喜歡的事﹐你會不會糾正他﹖」
「當然。不糾正不就變成溺愛了嗎﹖」張莉說。
「所以你對孩子的愛里就含有「不喜歡不義」這一點。那么你的孩子假設一時改不好﹐又犯同樣的毛病﹐你還會愛他嗎﹖」
「當然會呀。」
「對了。這就是忍耐。你不會因為孩子不能達到你的要求就不要他了﹐也不愛他了。聖經所說的忍耐就是這樣的忍耐﹐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不是出於無奈﹐迫不得已﹐而是出於恩慈﹐出於愛惜。
「當然孩子與先生是不同的﹐我們都不能用對待孩子的方式來對待先生﹐因為對於孩子﹐我們是母親﹐而對於先生﹐我們則是妻子﹐不能將在不同關系里面的角色混在一起﹐但忍耐的道理還是相通的﹐都是愛的道理。」
張莉不吱聲。
「我聽了你們的事后﹐覺得你們的溝通不太夠。你以前對李岩的確是有忍耐﹐不過從我有限的了解和印象中﹐你的忍耐好象比較消極﹐他并不知道你希望他怎么做﹐也不知道他做的不好的時候﹐你的感受是什么﹐等等﹐這樣的忍耐會讓你自己受不了﹐因為你忍了半天﹐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你在忍耐﹐不知道他得罪你了﹐傷到你了﹐所以不會有什么改進。而且這樣的忍耐到一定程度你就會暴發——是人都會暴發的﹐沒有人受得了嘛﹐是不是﹖這樣的忍耐對婚姻是沒有建設性的。你會覺得委屈﹐其實對對方也不大公平。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在積極溝通方面再努力努力。夫妻雙方其實不怕吵架﹐怕的是不會吵架﹐就是吵架的方式不好﹐吵的時候大家都只是圖發泄﹑圖痛快﹐而不是為了建設婚姻。你覺得我說的有道理嗎﹖」
張莉垂下眼睛﹐用雙手將頭髮往後面攏﹐嘴里含糊地吱晤了一聲。
「所以我覺得你是不是先不要急著決定離開美國。你們由戀愛到結婚﹐彼此一定有許多地方是很讓對方喜歡的﹐而且這些因素我相信還存在。為什么不給李岩﹑也給你自己一次機會呢﹖你要是什么都試過﹐該說的說盡了﹐該做的做完了﹐事情還是無法挽回﹐到時候再做決定你也會安心﹐對不對﹖
「再說你們都有孩子了﹐兩個鬧僵了﹐一邊是爸爸﹐一邊是媽媽﹐這讓孩子怎么辦﹖就是為了他的緣故﹐真的也需要再努力一下﹐是不是﹖」
張莉說﹕「道理是這樣﹐可是我真的覺得不公平。你在這里這樣勸我保全這個婚姻﹐他則不回家﹐而且去的是一個有外遇的人那兒﹐我不知道哪個人會怎樣勸他。要是我這樣去作﹐他卻反著來﹐那么我不是更委屈嗎﹖」
媛姐將張莉的手牽過來握著﹐說﹕「也許這樣想你就不會覺得委屈了﹕婚姻是雙方的﹐婚姻好懷雙方都有責任﹐好了雙方受益﹐不好了呢﹐雙方受損。你作為婚姻的一方﹐盡你這一方的責任﹐是本分﹐而不是吃虧﹐你說是嗎﹖至於結果怎么樣﹐我想你先盡了本分再說﹐不要猜測﹐因為很多事是我們猜測不了的。而且﹐凡事﹐總得有某個人先開頭吧﹐對不對﹖夫妻雙方﹐不是你開頭﹐就得他開頭﹐你來開一個好頭有什么不好﹖而且﹐你已經信了耶穌﹐是神的兒女了﹐也許﹐神揀選你做祂的女兒﹐說不定就是要你在家中來開這樣一個好頭也難講。基督徒都有聖靈的引導﹐你雖然剛信﹐聖靈也在引導你﹐只要你把這樣的事帶到禱告中﹐你會經歷聖靈的提醒和幫助﹐祂會幫你來做好。」
張莉沉吟半刻﹐問﹕「媛姐﹐你說的那對夫妻後來真的就特別恩愛呀﹐不是為了孩子的緣故或者其它什么原因將就湊合﹖」
「不是。他們很好。」媛姐以百分之百的語氣說。
「我認識他們嗎﹖我不是想探聽人家的隱私﹐你不需要給我他們的名字﹐我只是想這樣的人是不是就在我的生活里面﹐因為我也知道一兩對夫妻有過會婚外情的情況﹐後來還是在一起沒有離婚﹐但是夫妻的那種感情其實已經結束了。」
「這一對夫妻呢﹐你認識。而且很熟。」媛姐微笑著說﹐看著張莉。張莉也看著媛姐﹐有那么極短的一瞬間﹐她覺得媛姐的微笑是從遙遠的過去升起來的﹐讓她影影約約覺得媛姐講的就是她自己。可是怎么可能呢﹖看眼前的媛姐﹐大約五十來歲了﹐今天可能是要急著趕來見她﹐所以沒有象以往那樣上淡妝﹐皺紋有些明顯﹐但與媛姐那雙和善﹑安怡的眼睛配在一起﹐讓人感到的卻是笑意﹐感到這張臉的主人是個有福的人﹐那皺紋并不代表滄桑﹐而是多年幸福生活的證據。張莉自己其實就有過兩次小小的機會對這樣的幸福生活驚鴻一瞥﹐一次是去媛姐家參加姐妹會﹐媛姐的丈夫余先生正要出門﹐在門口與媛姐輕輕捏捏手﹐互相望了望﹐那個動作太小﹐不易察覺﹐張莉卻感動半天﹐因為小動作後面的大深情是顯而易見的。還有一次也是在媛姐家聚會﹐余先生在家休息﹐雖然沒有出席這個只有女人的聚會﹐可是卻下到廚房為她們這些女人做烤雞。大家誇謝的時候﹐余先生只是略帶緬腆地說﹕「平時小媛做得多﹐今天我在家﹐我可以做。」然後輕輕拍拍媛姐的肩﹐又去廚房為大伙兒燒茶。這樣的夫妻會有過差點發生慘案的歷史嗎﹖
張莉沒有追問下去﹐她只覺得自己的心沒有那么抗拒和叛逆了。媛姐又同她聊了許多﹐又帶她一起禱告﹐為李岩﹑李岩的學業﹐為她自己﹐為他們之間的關系﹐為他們的孩子…
所以﹐當媛姐走了﹐帶走的是張莉暫時不作回國打算的承諾﹐留下的則是她與張莉分享過的聖經經文。
